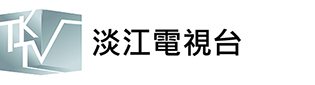重塑視障學生的創作可能
指尖緩慢移動,仔細確認立體線條的起伏。在台北啟明學校的美術教室裡,每週的「藝術生活課」成了視障學生探索創意的舞台。教務處主任張銘富在這間教室已耕耘七年,他對於教學有著簡樸卻深刻的信念:讓每一堂課都成為學生動手實踐、親身體驗的機會。
「學生因為受限於視力,我不想讓他們像外面的學生一樣去學藝術史、研究藝術家背景。」張銘富說,「我的精神就是讓學生在每節課都能動手操作、做創作。不管做多或做少,希望他們都能親身體驗,把自己的想法透過雙手做出來。」這種強調實作的教學方式,反映了他對視障學生能力的深刻信任。
然而,要讓這樣的教學理念真正落實,需要有系統的教材與完善的教學方法。過去十多年來,非視覺美學教育協會創辦人趙欣怡正在努力開發這樣的資源,而她之所以投入這個領域,源於一次特殊的相遇。

攝影/馬芷寧
因緣際會 開啟非視覺藝術創作的新可能
2006年,趙欣怡認識了台灣視障藝術家廖燦誠。「我做觀察與研究,想瞭解他在非視覺的狀態下如何持續進行創作。」她回憶道。正是這次的機緣,使她將廖燦誠的創作方法引介給視障學生。
這個過程中,趙欣怡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。「這些學生其實是有能力的,只是通常大家都認為他們看不到,就不太可能進行視覺藝術活動,所以自然而然覺得他們不需要這樣的課程。」她指出,這樣的認知落差成了視障學生接觸藝術教育的第一道高牆。

攝影/馬芷寧
尊重自主權 打破「幫助」中隱藏的決策權剝奪
儘管教室資源有限,但趙欣怡與張銘富都堅守一個重要的教育原則:尊重學生的自主權,而不是直接告訴他們「樹是綠的」。
趙欣怡在課堂上採取了一個看似簡單卻充滿深意的做法。「我通常只給學生三原色跟黑白。」她說,「但很多人在幫視障者上課時,會直接告訴他『這是樹,所以我給你綠色』。這樣學生就沒有決定權——他可能想用白色呢?或許他想畫的不是夏天的樹,而是冬天的樹。」
這個微小的改變背後,蘊含著深刻的教育哲學。「自主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,」趙欣怡強調,「視障學生不應該被決定,他們應該有選擇的機會。」

攝影/馬芷寧
故宮合作 一年的沉浸式文化體驗
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,台北啟明學校與故宮博物院展開了一項特別的教學合作。從認識青銅器、甲骨文、金文的形體開始,師生們花了整整一年,最終創造出一件兼具聽覺、視覺與觸覺豐富性的大型樂器裝置藝術作品。
張銘富描述了這個創意過程。「故宮的志工老師進來帶高三學生體驗青銅器、甲骨文、金文等文字的形體。我們隨後與同學利用前一個月所學的東西進行創作。」他說,後續還有一件更大型的作品,結合編鐘的樂器概念,先生成骨架,然後蒐集很多回收物固定上去,讓它能發出聲音。
這個合作不僅是一次藝術創作,更是對視障學生創作能力的一次完整展現。通過觸覺感知古文明的紋理,透過聲音轉譯文化的涵義,盲生們用多感官的語言重新詮釋了傳統文化。

攝影/馬芷寧
明盲共融 感官互補的雙向學習
非視覺美學教育的另一個關鍵理念是「明盲共融」,這是趙欣怡在課程設計中特別強調的。讓明眼人與視障者在同一個空間,透過各自的感官優勢,互相學習與引導,這個過程中也自然消弭了社會的成見。
趙欣怡解釋了這種共融的深層意義。「視障者可能會仰賴明眼人的視覺輔助,但明眼人其實也很缺乏觸覺刺激與聽覺訓練。通過參與這樣的課程,明眼人可以理解如何透過這些方式增加自己的感知能力。」她說,「這不是單向的幫助,而是一種共學。」
在這樣的交互學習中,視障與明眼不再被視為絕對的差異,而是互補的優勢。明眼學生因此發現,自己對觸覺和聽覺的敏銳度遠不及視障同學;視障學生則體驗到,自己的感官世界與明眼人一樣豐富多彩。

攝影/馬芷寧
從侷限到無限 藝術的多感官轉譯
當藝術不再侷限於視覺,「看不見」的限制就被打破了。透過多感官的轉譯、對自主權的尊重,以及社會各界文化機構如故宮的共同投入,視障學生正在黑暗中綻放出最耀眼的藝術光彩。
張銘富與趙欣怡的努力證明了一個簡單卻深刻的教育真理:限制往往來自於社會的預設,而非個人的能力。當教育工作者願意看見學生的潛能,當社會願意提供平等的機會,當文化機構願意打開大門,視障學生就能在藝術的世界裡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與光彩。
延伸閱讀:
更多報導請看:淡江新聞